宋生贵:迎春笔谈
每每喜迎新春之际,心间即有美好期待。此刻,久久静坐于书案前的我,脑海里活跃起一个意念:“诗意”。与这个意念相伴而生的,是一些意象,有文思与艺趣方面的,也有人生情味方面的,当然都是美好的,向善的。
一、关于“诗意” Welcoming Spring Essays 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曾经格外深情地说:“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诗句经海德格尔在他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着力阐释而广为流传,更加引人关注。显然,这诗句所传达的是人类的美好的生存状态,也是人类期望与追求之中的境界。 那么,我们现在追问一下,人类祖先的生存实践之中从何时有了对于这“诗意”的追求的呢?在我看来,要回答出具体的年代是困难的,但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论判断:人类最初的诗意起始于美意识的生成之时——需要特别指出,这里讲的是“诗意”而不是“诗”。如果说美意识的生成标志着人类开始对于外在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世界有了精神意义上的感悟的话(包括非自觉到自觉),那么,“诗意”便是激活于那精神空间的自由的精灵。 有了“诗意”,人类生存实践中便有了对于一般生物那种满足本能欲求的超越,同时也有了情,有了趣,有了灵性,有了富有美的内涵的精神张力,以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并拥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而且,通过历时性的反观可以发现,哪个时期、哪个地域、哪个民族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富有诗意,其文明程度就高,为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亦丰富灿烂,反之则不然。 “诗意”是一个富有美学色彩的概念,令人情牵意动。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如文学中所讲的“诗无达诂”、诗无定规一样,现实生活、生存中的诗意也是见仁见智的。但在我看来,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会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又往往正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从庄子体悟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再到西方人感受到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世界”(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语),可谓是对于富有诗意的生存状态的传达。这主要是体现了人与自在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自由相适。 陆抑非《水仙》 当然,人类的生存并非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必然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所谓“充满劳绩”,就是实践行为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待自然——从自在的自然到人化的自然。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多彩的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正是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到了近代以来,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 按照我的体验与理解,人类是否可以“诗意”地生存于世,追问到底,则要看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心之间,是否具有自由和谐的空间,以至是否能够建立起富有审美特质的关系。当然,人与自然环境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则又是形成“诗意”之质的重要前提或根源。自然是一切自由的永恒基础,人与自然的联系是生命的渊源。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在人类社会中自然环境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它“对人类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从自在的自然到人化的自然,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包含着人的自由的实现过程。 人类终究还是向往富有诗情画意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状态的。但这需要人类为之付出永不休止的努力,其中首先要努力维护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这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本原。为此,即需要特别强调遏制人性中的贪欲。因为它是扼杀“诗性”或“诗意”的罪恶之源。它可以使自然变质,使自由窒息。对于急功近利的现代人,对于过热的消费社会和金钱理性来说,尤其是需要以加倍的努力去制约和调适的。说到底,关键处就是要实现对于人自身的调节,而调节的重心则是要抑贪欲,扬诗性。这可以称作是一种新的生存理性的自觉! 二、关于审美 Welcoming Spring Essays 审美,需要有独到的眼光。 所谓独到眼光,当然并不单指看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什么。譬如,水浪与礁石扑打在一起,水浪被摔成碎沫,礁石也承受了刀砍斧斫般的冲击,我们各自会从中看到些什么,发现些什么?诗人艾青与散文家杨朔都观察到此种景象。其中,艾青有感于为坚持真理而傲然挺立的志士,从礁石上发现了不屈之美;而杨朔有感于水滴石穿、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便从浪花中看到了顽强之美。于是,艾青有精美小诗《礁石》,杨朔写出散文《雪浪花》。其中便含蕴有美感上的辩证关系。 生活,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如果打比方,它是一曲旋律复杂而动听的歌,是一幅多色调多层次的画,抑或是茫茫瀚海和它怀抱中的航船。但它们所蕴含的是同一个生活内核——真、善是它的底蕴,美是它的艺术化呈现。 夏夜里头顶上横跨天际、灿烂飘逸的迢迢河汉;在薄云里若隐若现、沉静明丽的皎皎圆月;峻峭挺拔、参差错落的嶙峋怪岩;几经海潮琢磨,晶莹玲珑的卵石;抑或傍晚时分抹在西天边奇幻的光彩,或疏影斑驳间生动的倩影,都是美的。大山名川、名胜古迹不必说,就是一簇馥郁芬芳的丁香,一池清露流转的荷叶,溶溶月色中传出的蛙鼓,清幽山林中的蝉鸣,都含蕴美妙的诗意。一支嘈嘈切切的琵琶曲,一幅墨韵生动的山水画,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一首意境优美的抒情诗,更是生活的概括反映,是美的升华和结晶。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是有道理的。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容易因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使得审美视界变得狭窄,与之相关,其创造力必然受到局限。真正鲜活而独特的美感的获得,是需要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用自己的眼睛乃至整个身心去体察与发现的。 三、关于写作 Welcoming Spring Essays 在物理概念中,时间是绝对的,无情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声浩叹穿越久远,令人心惊,但无奈依然。时间如水流逝,一刻不止,古希腊有哲人讲:“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生活便是时间之河中的一个个片段,随流而去。人生活在时间里,而时间的背后则隐藏着许多玄机,如少年的雄心,佳人的美丽,志满意得者的前程等,都有可能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中国古人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就是因为岁月无情,光阴不再。 齐白石《兰花》 在我的体认中,写作则可以使岁月生情,让时光生趣。一方面,每当进入写作状态,我便常常会游离于物理时间之外,让想象和思绪带入自己缔造的世界,并因此而生成独特的、新的时空概念。在此,时间进入了心灵内部,用以营造个人化的精神生活,所以,时间也便自然有了诗的意味。另一方面,写作可以让我感到在时间的河流中过得踏实,以奇妙的文字表达出自己的发现与情思,由是便在与时间的博弈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纷纷扰扰的白天,还是长夜如歌的夜里,一张桌,一支笔,一杯茶,专注于自己心仪的领域,把纷繁杂扰的诱惑关到窗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真实的心情付诸字里行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赴约,是一种境界,一种承诺,一种指向。有了这样的心灵安顿,每当对待世间的诱惑与个人的荣辱得失时,则可以显得淡然或超脱些。当然,现实中的每个人,都要以不同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在时间的河流中游走,各自的体验会有所不同。 关于生命空间的扩展,这是我一直以来所认定的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所在,并通过学术研究加以阐释。当然,命题的起点还是来自现实:人生苦短,天地久长,万物皆变,一切皆流,人若仅只限于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物质性把握和实用性开垦,则必然陷于压抑的、自视渺小的悲观或困顿之中,所以,便需凭靠伸展精神的双翼飞向远方——此可谓人性深处的一种强烈的冲动,所指向的正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天地间永恒的精神相融合,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让生命的意义在自由无碍的空间升值。可以说,这正是人类从事文化活动,特别是文学艺术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永恒性的心理及哲学依据;也是人类生命情调中的一个绿色命题。 无论如何,足迹都会留在身后,需要迎接的是明天——岁月,在充满生命律动的新陈代谢中有了魅力;人生,因富有活力的创造与奉献而生出诗情画意。何其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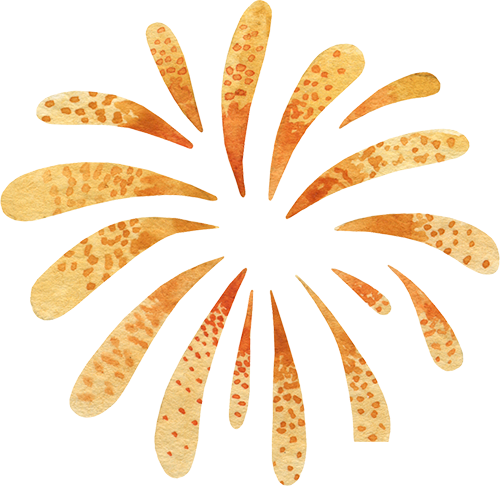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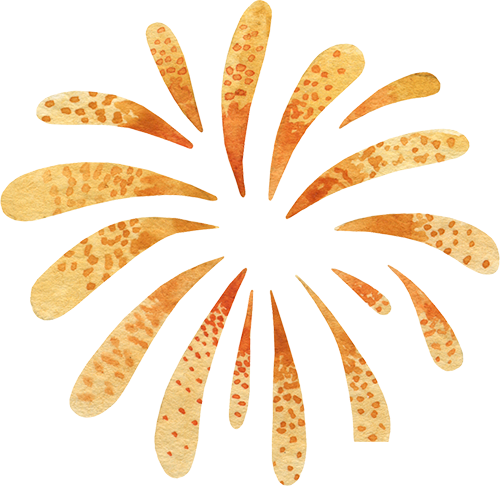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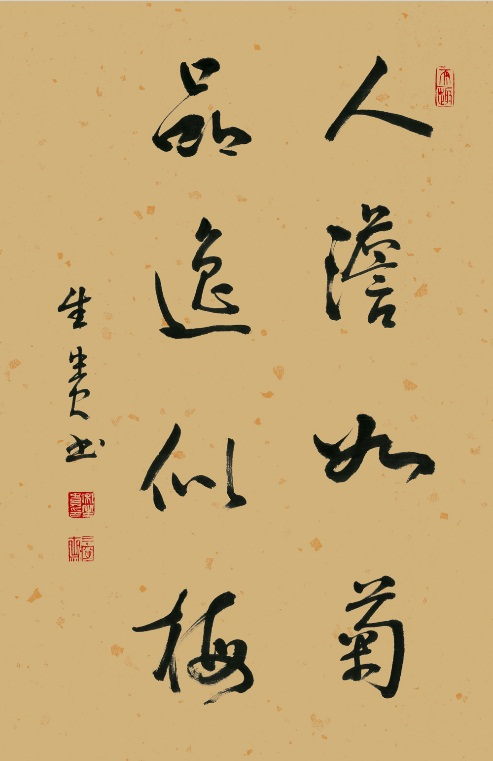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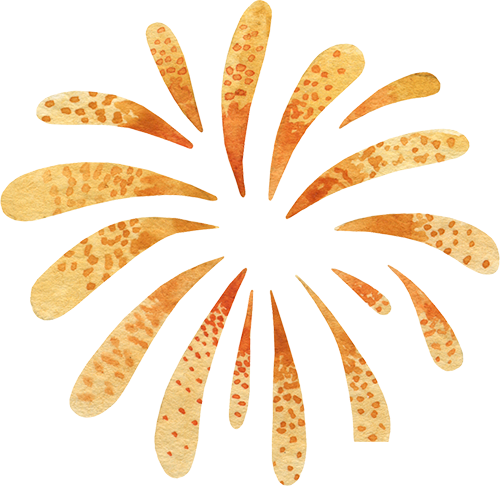



(图文来源: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